1.「General or universal?区分两种“普遍”」

《哲学研究》
作者:[奥] 维特根斯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16年
3.「机制:一种特殊的“普遍性”」
单讲共同点本身也有着不同种类的共同点。
刚才我讲到了,比如说3、3、3这些数字有一共同点,它们都是3。但是还有一种共同点,给你两个数列,说这两个数列有什么共同点?比如2、4、6、8、10和3、6、9、12。它们都是等差数列,相邻两个数的差是不变的。
这种共同点已经不太像都是3然后抽象出一个3来,这种我们把它叫做关系共相。再给你一个数列:1、4、9、16、25、36。当然可以更复杂一点:2、6、12、20、30、42。这数列,你不一定一下子就能看出一个规律,实际上它是n²+n的展开式。
我们先有共相这个概念,就好像(共相)是好多事物的共同点,然后我们就有这种关系共相,关系共相我们经常就把它叫做规律。
2、4、6、8和3、6、9、12,虽然两个数列本身不同,但是它的规律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好像我们从这种共相概念深一层地到了规律的概念。然后我们现在给出了一个n²+n,我现在要问,n²+n的展开式是有规律的还是没规律的?我觉得说没规律可能不是太好,但你说它是有规律的吧,它没有什么一眼可见的规律。
越复杂的公式,我们就越想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内在规律。但是“内在的规律”这个词对我来说稍有点别扭,因为规律这个词本身是相当表观的。你看上去有规律就是有规律,要是看上去没规律,它就已经差不多没规律了。当然这后面就有个公式,也用不着编词,它就是公式。但是要放在我的其他的一些想法中,我会把这个公式就叫做mechanism,就是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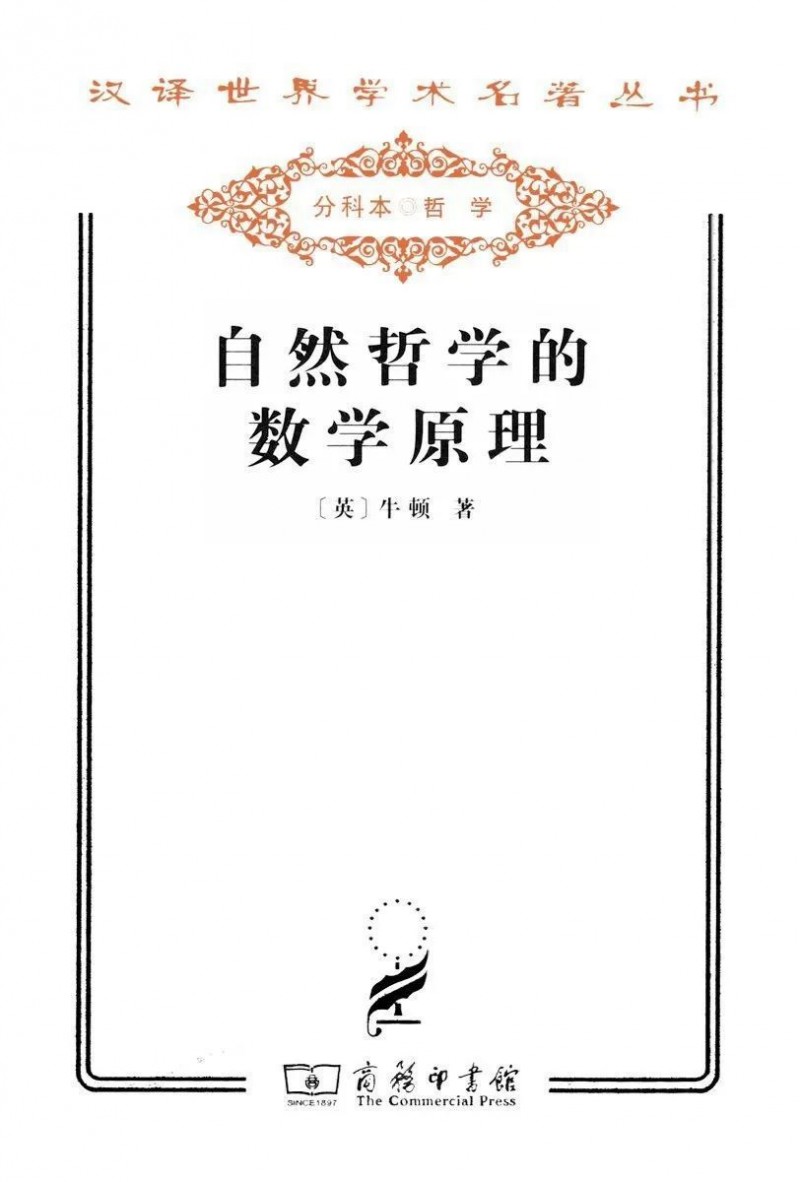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作者:牛顿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11年
这种mechanism就是我们所讲的共相、共性的最后一层意思了,这时候你把它叫做普遍性、共相、共同点就很勉强了。因为这公式并不是这些数的一个共同点,你差不多就得转换你的想法,转化你的词,你就直接把它叫做一个公式,或者叫做一个机制。它背后有个机器。
在一个意义上规律已经跟必然性差不多连着了,好像说规律就是必然规律似的,你说偶然规律这话都不通。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规律并不是事物的解释,而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事情。
我大概就这个意思:这边发生了一个凶杀案,我是警探就在蹲守。然后我看张三每天晚上九点钟他都到这房子跟前转一圈,然后走了。我蹲了一礼拜,发现这就是有规律的。他这种有规律的活动对我是一个提示,means something,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偶然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必然性恰恰是在等着去理解的,而不是说已经理解。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上的必然性它到底有什么道理。
科学不是为了发现规律,而是要想去理解到底怎么就来了这规律,张三为什么每天到这儿转?作为自然科学来说,它是发现了这个公式,发现所有这些有规律的现象背后都是有一个机器的。
这个机器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仅解释了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有规律的现象,也解释表面上看起来没规律的现象。在表观上你把事物分成有规律的和没规律的,等到真实地掌握了那个自然机制之后,你发现没有什么是没规律的。它只是机器调换了参数之后,生产出来了不同的东西而已。
4.「我们要达到的是一种翻译的普遍性」
那么现在我们的理解是,哲学中的普遍性不是这样的一种普遍性,我们要达到的是一种所谓翻译的普遍性。
任何一个语词都是某一种语言的语词,英语词或者汉语词。如果把语言想象成一个网络,一个语词就是网络的一个节点,好多线头它连到一个节点,不同语言中的节点是不同的。
一般说起来,除了专有名词之外,没有两个词是正好叠加在同一个坐标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有一个汉语词正好对应英语词。但是这两张网你要宽泛地说,却可以大致起到同样让人满意的效果。
比如英语里有belief、faith、conviction,拿到汉语里怎么翻译都不对。你说belief,你把它翻译成看法,它比看法稍微强一点;你翻译成信念,它比信念(弱一点),信念得多强;但你要翻成信仰就更不像话了。
英语把这几个概念布局在那儿,大致就能够用来说它要说的事。我们可能就是有看法、意见、信念、信仰。虽然这些词都不是一个意思,没有一个词(和belief)对着的,但我们这么组合就能把我们大致要说的事也说了。

《星月夜》文森特·梵高(1889)
我们有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一种翻译方法就是table统统翻译成桌子,不是table统统不翻译成桌子,这个时候“桌子”就变成了table的一个汉语对应词。这个词看上去像汉语词,实际上是个外语词。它的概念联系是在英语里面,它是在英语网里的一个节点,汉语里本来没这个东西,我们造一个新的节点专门为了对应table。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这么干,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不属于汉语这个系统,我们在汉语里用它就别扭。
另外的一种,正常的翻译大概就是按照上下文来翻译这个词。而这个就是我所原意理解的普遍性。
当你说英文的“table”和汉语的“桌子”之间有一种共同点或普遍的东西时,它既不是那个抽象的普遍性,也不是机制的普遍性。你想说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说汉语的“桌子”跟英语的“table”是通着的;汉语的“书”跟英语的“book”通着的。
书和book这两个概念各有各的概念内容,把它想象成为一个面积,然后它们两个的叠加会有一个共同的部分,这个共同的部分就是它们两者都普遍的东西。book和“书”这两个字它重合不重合呢?最关键的是它重合的部分,没有一个词来称它的重合的部分。
你只能理解书或者理解book,你在汉语里理解书,你在英语里理解book,然后你再理解book和书相通,你并不理解它们俩共同的重合的那部分,因为它不是一个概念。
那个共同性的东西不是你要理解的东西,你理解的永远是特殊性的东西。我们总是想着通过特殊性去理解普遍性——“我们上升到普遍性”。这是我从根本上反对的一点。为什么要去理解那个普遍性呢?干吗要上升到普遍性呢?
我现在想说:我们就是在理解特殊性,我们就是在理解“book”这个词,就是在理解“书”这个词。然后我们在理解特殊性的同时,看到了什么特殊性跟什么特殊性是通着的,在什么程度上是通着的。我们一开始对普遍性的理解更多的是用“同”这个概念,我想这个故事整个讲完,我们就(能)逐渐更多从“通”的角度去理解了。
